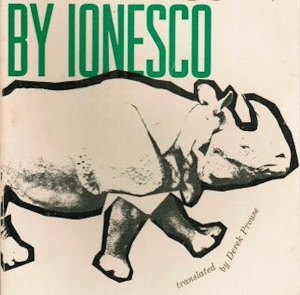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预计最高法院将严格限制联邦政府监管温室气体排放的能力。 尽管美国几乎完全没有关于气候变化的严肃政策,但 26 个州和化石燃料行业团体仍在争论 西弗吉尼亚州诉环境保护署 奥巴马总统现已失效的清洁能源计划是对各州权利和国家能源经济运作的不允许的侵犯。 该案例及其后果对于理解资本如何维持其对地球命运的灾难性控制以及为什么左派必须直面气候正义的主要障碍之一:化石法非常重要。
“化石法”是指与物理基础设施一起将二氧化碳从地球转移到大气的规则、法规和原则。 化石法与全球资本主义一起成长,它迫使化石燃料的持续开采和消费。 它不仅通过限制环境法规的范围、阻止对气候污染的责任以及将公共资源转移给工业来做到这一点,而且还将抵制化石燃料系统定为犯罪。 为了实现对任何 21 世纪社会主义计划至关重要的气候正义目标,左派必须瞄准化石法的主导地位,并参与一场战略性气候法律行动主义运动。
化石法可以在口头辩论中看到 西弗吉尼亚诉 EPA,其中最高法院正在考虑环境保护署在《清洁空气法》下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监管有多少自由裁量权(预计将于 6 月作出裁决)。 布雷特卡瓦诺法官质疑该机构处理“重大问题”的权力,例如电网的能源构成,表达了对法院极右翼绝对多数的怀疑。
我们说过的一件事 [in a previous opinion curbing the EPA’s authority to regulat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是国会如果希望分配具有重大经济和政治意义的机构决定,就必须说清楚。 我们说的第二件事是,当各机构声称在一项长期存在的法规中发现了一种不为人知的权力来规范美国经济的很大一部分时,法院对此表示怀疑。
换句话说:任何严格的气候调节都会产生广泛的经济影响。 干预市场本质上是可疑的。 因此,如果没有国会的明确指示,美国环保署在减少燃煤电厂的排放或迫使整个电网转向可再生能源方面无能为力。
鉴于近期气候立法行动的历史,将责任推卸给国会有点丰富。 但气候监管问题比腐败立法机构的不妥协更广泛:它触及现代环境法的核心。
我们今天认为的环境法的大部分内容——比如《濒危物种法》和《清洁水法》——源于国会在 1970 年代初期通过的一系列立法。 当时,两党一致通过立法支持改善空气和水质、保护野生动物和减少行业滥用。 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倡导并签署了《国家环境政策法案》等法律,旨在“鼓励人与环境之间富有成效和令人愉快的和谐”。 环境保护署于 1970 年开始实施一项新的监测和监管计划,联邦政府为自己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例如到 1985 年消除通航水域的所有污染。
美国环境法取得了许多成就:与 1960 年代相比,我们今天的空气中铅和二氧化硫的含量要少得多,可供游泳或钓鱼的美国水道数量是 1960 年代的两倍。 气候律师和立法者与赔率进行了令人钦佩的斗争,对碳排放巨头提起了侵权诉讼,并在州一级通过了重要的变暖限制。
然而,自 1990 年以来,国会没有批准任何重大的环境立法。 它从未通过关于气候变化的主要法律。 《清洁空气法》,有争议的法规 西弗吉尼亚诉 EPA,没有提到全球变暖,它的工具——尽管适应性强——从根本上不适合温室气体问题的扩散和长期性质。 在这一点上,卡瓦诺等法官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我们需要更好的法律。
但化石法作为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方法的基本法律结构,挡在了路上。 这是因为,与全球变暖的社会现象一样,它是工业革命以来经济爆炸性扩张的副产品,它共享一个位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根源的基本密码——产权、个人主义和私人企业。
产权保护有害的经济活动以及开采技术和能源生产的所有权,并使法律体系偏向于利润而不是社会利益。 个人主义塑造了在法庭案件中的站立规则,禁止任何无法证明直接、直接伤害的人诉诸司法(在气候变化方面很难表现出来)。 私营企业享有法人身份的法律虚构和对公共土地和补贴的开放使用权。 我们十八世纪的宪法没有提到保护自然世界; 事实上,我们的联邦环境法是基于国会监管州际贸易的权力。 在司法驳回气候变化案件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该守则的力量。 如果最高法院甚至认为 EPA 的适度干预是对现行环境法的非法应用,那么除了推动法律的当前限制之外,我们还必须从根本上更新其雄心和范围。
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 与任何称职的左翼理论一样,气候正义法的社会主义计划应该寻找已经从社会斗争中出现的答案。 虽然任何特定活动的细节各不相同,但气候法律行动主义战略将法庭内外的工作团体团结起来。 他们将基层的抵抗与对私有财产权、陈旧的地位规则和联邦对污染行业的尊重结合起来的雄心勃勃的法律挑战——并提供了保护自然和对经济计划进行民主控制的权利。
例如,明尼苏达州 Ojibwe 地区的 Enbridge 3 号线管道之争产生了关于如何判断我们对环境的使用的激进的新想法。 十年来,数千名原住民领导的抗议者的抵抗最终导致直接行动停止管道的建设,该管道穿过敏感的湿地,将锁定对焦油砂油的需求。 这场运动最终没有成功; 管道已经建成。 但活动人士并没有投降。 在法庭上——他们面临重罪盗窃等指控——一些人争辩说,他们对石油基础设施的“非法”干预是基于保护野生稻的正当理由,野生稻是奥吉布韦文化的核心植物,并且面临管道泄漏的风险。 这些激进的被告声称,根据联邦政府与白土乐队在 2018 年对这些权利的承认,野生稻享有自己的合法权利。一项质疑政府批准管道的相关诉讼也是基于相同的前提。
左翼气候法律战略也可以向世界其他地区寻求战略,尤其是在美国法律体系是化石法最重要堡垒的时候。 2008 年,厄瓜多尔成为第一个在宪法中承认自然权利的国家,这是一项植根于土著和非裔厄瓜多尔社会运动的实验; 自 2012 年以来,玻利维亚一直在进行类似的过程。去年年底,厄瓜多尔宪法法院阻止政府出租洛斯塞德罗斯受保护森林的采矿权,认为此类特许权将侵犯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的权利。
当然,这些努力并非没有局限性和矛盾:例如,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环境制度因侵犯土著主权而受到批评,而自然权利运动尚未证明其实际效力或解决有关它依赖于基于权利的变革理论。 但该项目的不稳定性质并不是放弃该领域的理由。 具有丰富的社会主义法律理论和实践传统。 左派的关键是要避免法律自由主义(根据法律引导正义)和教条式的反法律主义(拒绝所有作为妥协主义者的法律倡导)的双重诱惑。
与司法机构内外斗争——在法庭上积极争取新的权利和权利,并在街头直接对抗化石燃料行业——是我们推翻化石燃料法的最佳机会。 鉴于最高法院对民主、经济正义和生殖权利的攻击日益激烈,这可能是挑战美国法律体系合法性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 打破法律,重新制定法律,收回法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起草我们应得的未来。
Source: jacobi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