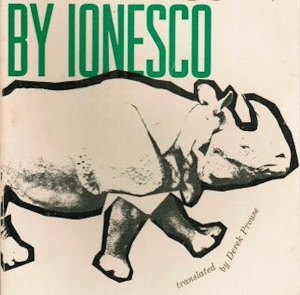2022 年 5 月 8 日,在麦迪逊威斯康星州家庭行动办公室的外部喷涂了“如果堕胎不安全,那么你也不安全”。
照片:亚历克斯舒尔/威斯康星州杂志通过美联社
当我阅读 一个自称为简的复仇的组织在麦迪逊、威斯康星州、得梅因、爱荷华州以及从华盛顿州到华盛顿特区的其他地方对反堕胎“危机怀孕中心”进行了燃烧弹轰炸,我的第一个想法是: 什么鬼?
这是假旗吗? 除了在其恐怖分子军队谋杀堕胎提供者时视而不见的极右翼之外,还有谁会玷污简的名字,这个芝加哥集体在罗伊诉韦德案之前提供了 11,000 多例安全、非法的堕胎? 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策略:支持选择力量的暴力运动将强化堕胎倡导者作为野蛮人的形象,并证明对那些实施、促进或进行堕胎的人进行严厉惩罚是正当的。 想想看,世界上是否有人以生育自由的名义投掷过燃烧弹?
或者简的复仇是第一个——地下气象的无政府女权主义后裔,民主社会学生的分裂,在 1960 年代和 70 年代美国侵略越南时轰炸了大学和政府大楼、银行和其他合作者? Weather Underground 发誓只伤害财产,而不是人。 但不可避免地,生命因其拙劣的英雄主义而丧生。 简的复仇会不会有类似的结局?
新闻报道表明了不同的怀疑态度。 主流媒体大多对这个故事置之不理,而天主教媒体、华盛顿时报和福克斯新闻则在报道。 在 5 月 15 日的每日播客“它可能发生在这里”中,报道极端主义的罗伯特·埃文斯回顾了该组织公报的语言及其来源,并表示相信简的复仇是它说的是什么,而不是一些右翼冒名顶替者。 埃文斯称这些行为为“道德恐怖主义”——破坏“基础设施”而不是针对“平民”的“不道德恐怖主义”——同意一位客人的观点,威斯康星州袭击者的炸弹是“相当不错的燃烧弹”,并宣布采取行动“胜任”及其传达的信息清晰。
在堕胎权利倡导者中,简的复仇——不管他们是谁——得到了可以预见的褒贬不一的评价。 “我们保护持续获得生殖保健的工作植根于爱,”威斯康星州计划生育协会主席在麦迪逊爆炸事件发生后表示。 “我们谴责社区内一切形式的暴力和仇恨。” DSM Street Medics,一个位于得梅因的医疗保健机构, 发推文 Jane’s Revenge 于 6 月 9 日发表的公报。帝斯曼的评论:“我们绝不参与这些行动,但我们为它们鼓掌。”
我的感觉并不完全符合这些。 当爆炸的消息传出时,像许多美国人一样,我拖着自己到处走,对布法罗、乌瓦尔德和塔尔萨的枪击事件感到恐惧和绝望,确信国会几乎什么都不做,最高法院可能恶化裁定枪支条例违宪的大屠杀。 简的复仇在被毁坏的建筑物的墙上潦草地写着威胁—— 如果堕胎不安全,你也不安全 ——只会增加我的恐惧。 这是迈向所有人对所有人的霍布斯战争的下一步吗?
然而我承认:他们的言辞对我说话。 他们的目标特征令人耳目一新。 位于得梅因的 Agape 是一家“宗教假诊所,对需要医疗保健和支持的人施加情感、经济和身体暴力。 他们撒谎、羞辱和操纵人们不堕胎。”
他们的分析是正确的。 乌瓦尔德小学枪击案“是男性统治和父权制暴力的行为,旨在让妇女、儿童和教师生活在恐惧中。 我们知道,这与一个建立在白人男性至上的非法机构即将在这片土地上发动的生殖暴力密切相关,”该组织网站上发布的行动呼吁中写道。
虽然几乎没有掩饰对暴力的呼唤让我感到害怕,但对情感的呼唤指出了问题,并开始了解决方案。
我的愤怒和不耐烦和他们一样炽热。 我也对主流的“端庄的争取自由的小集会”感到恼火——5 月 11 日的示威活动让我更加沮丧而不是精力充沛——并且厌倦了“在我们的愤怒被……引导到民主党筹款活动时袖手旁观”。 我对他们的语言感到兴奋—— 愤怒,愤怒,凶猛 ——以及他们宣称“我们需要他们害怕我们”。 虽然几乎不加掩饰的暴力呼唤让我感到害怕,但对情感的呼唤指出了问题,并开始了解决方案:“无论你的愤怒采取什么形式,第一步就是感受它。” 作家和活动家 Alix Kates Shulman 曾经谈到女权主义愤怒的兴奋——“愤怒的异常”。 当 Jane’s Revenge 发泄我的愤怒时,我从不知道自己持有的焦虑中解脱了出来。
但现在呢?
我们不知道简的复仇行动是相互协调的还是相互独立的。 公报谈到“那些可以怀孕的人迫切需要学习如何直接面对厌恶女性的暴力行为。” 它敦促“忘记我们的自我控制……从街头开始。” 一旦你感到愤怒,该组织劝告,“下一步就是将这种愤怒带到世界上并用身体表达出来。” 我们如何直接面对厌恶女性的暴力? 我们应该如何在身体上表达愤怒? 除了“以身作则”之外,Jane’s Revenge 还建议采用 DIY 战术方法。
和策略? 播客埃文斯说,信息很清楚——但我认为他指的是文本。 轰炸本身呢? 它对谁说话? 简的复仇在为谁说话? 他们想吸引谁? 他们愿意留下谁? 暴力赢得了一些朋友,也失去了一些朋友。 除了在敌人心中引起恐惧之外,最终的游戏是什么? 有结局吗? 对我来说,这个信息一点都不清楚。
“愤怒之夜”,简的复仇给 6 月的“危机怀孕中心”爆炸案起的名字,显然是对气象员在 1969 年 10 月审判期间在芝加哥组织的“愤怒的日子”的致敬。 阴谋八. 这些行动包括砸碎汽车、商店和满是顾客的餐馆的窗户,与警察肉搏,以及计划入侵董事会办公室。 愤怒的日子是失败的:投票人数很少,警察压倒了抗议者,并且阻止了选秀委员会的闯入。 最后,这些行动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反而进一步疏远了 SDS 和黑豹党,其芝加哥主席弗雷德汉普顿谴责该派系是“革命儿童游戏”中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涉足者。 汉普顿警告说,气象员“正在引导人们陷入他们没有准备好的对抗中”。 事实上,1969 年 10 月预示着该组织将陷入更加鲁莽和致命的暴力之中。
凯西·布丹是地下气象组织最具魅力和最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她坚信印度支那的战争以及国内反对黑人和棕色自由战士的战争不会没有武装斗争就结束。 1981 年,她驾驶逃亡面包车抢劫了布林克的一辆装甲卡车,她的同伙,黑人解放军的成员,开枪打死了一名保安和两名警察。 边缘人的抢劫可能并不意味着是致命的行为。 布丹没有带枪。 抢劫发生时,她甚至不在现场。 然而,她在监狱里度过了二十年,在那里她花了无数个小时努力理解并为她认为是可怕的错误承担责任。
就像地下气象组织一样,简的复仇知道它的运动需要变得更加激进。 然而,它犯了将好战与暴力混为一谈的错误。 生殖正义运动如何在不升级我们的策略以模仿我们的对手的情况下变得更加激进——而不以更多的暴力应对暴力?
在不升级我们的策略以模仿我们的对手的情况下,生殖正义运动如何变得更加激进?
一个例子可以在 Jane’s Revenge 的另一个灵感中找到:芝加哥的 Jane Collective。 正如美丽的电影“The Janes”所展示的那样,集体中的女性为每位客户提供了富有同情心、尊重和孜孜不倦的优质堕胎护理。 简收取了病人可以支付的费用,包括不收费。 当她们决定组建简时,大多数女性已经参与了民权、反战和女权主义活动。 有些人冒了身体上的风险,在芝加哥的民权游行中面对投掷瓶子的质问者,或者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自由骑行中前往密西西比州登记非裔美国人选民。 他们要做的不是微不足道的违法行为:堕胎在伊利诺伊州是一项重罪,每次指控都会受到 1 到 10 年的刑罚。 但他们像往常一样对女权主义政治感到沮丧。 就像简的复仇一样,他们渴望直接行动。
Janes 提供了必要的服务,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服务机构。 他们认为自己是非暴力公民不服从的践行者。 “我们有一种哲学义务……不尊重一项不尊重女性的法律,”一位在影片中接受采访的女性说。 另一位成员称帮助一名妇女结束怀孕并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是“一种革命性的行为”。
对于布丁来说,“边缘人的卡车事件和她的被捕引发了危机和转变,”瑞秋·贝达德在《纽约客》中写道,但这并没有削弱她对激进社会变革的承诺,她在整个监禁期间的服务和组织中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当她最终在 2003 年获释时,布丁继续为正义而努力,直到她因上个月杀死她的癌症而变得虚弱。 “她学到的教训不是‘我不应该把我的生命奉献给斗争’,”布丁的儿子切萨告诉贝达德。 “她从悲剧中明确地学到的教训是‘暴力没有生产力。’”
Source: theintercep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