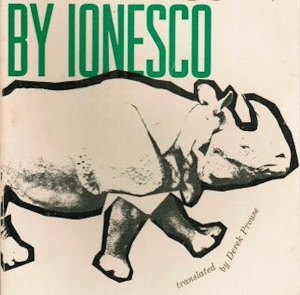照片来源:来自英国伦敦的 DAVID HOLT – CC BY 2.0
库尔德人正遭受乌克兰战争带来的最大附带损害。 乌克兰难民吸引了全球关注,但乌克兰战争为大规模驱逐 200 万叙利亚库尔德人敞开了大门,这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发生。 土耳其威胁要从五年前开始对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进行种族清洗。
土耳其领导的部队已经迫使数十万库尔德人逃离他们在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叙利亚一侧的飞地。 “没有地方放 [Kurdish fighters] 在叙利亚的未来,”埃尔多安说。 “我们希望……我们将消除该地区的分裂主义恐怖。” 在实践中,土耳其此前入侵叙利亚的政策一直是驱逐所有叙利亚库尔德人、平民以及武装分子、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
在土耳其取消了对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否决权之后,北约列强比以往更不可能阻止埃尔多安再次入侵叙利亚北部。 从长远来看,他们希望招募土耳其作为对抗俄罗斯的盟友。
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叙利亚库尔德人抛给了土耳其,尽管正是他们提供了地面部队,与美国结盟,在叙利亚击败了所谓的伊斯兰国,并在战斗中损失了 11,000 名库尔德士兵。
叙利亚库尔德人自己对他们可能的命运毫无疑问,许多人已经在寻求逃跑。 他们的种族清洗是乌克兰战争造成的最重要和最悲惨的附带损害,而外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一点。
我们采访了库尔德家庭的四名成员——父亲、母亲、儿子和儿媳,了解他们五年来第三次试图逃离即将到来的土耳其进攻时的经历和感受。 这一次,他们被迫从叙利亚东北部最大的库尔德人口中心卡米什利搬到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的首府埃尔比勒。 他们对命运的悲哀反映了各地难民的感受。
由于他们面临多重危险,所有姓名和识别他们的其他信息都已被删除。
父亲
我今年 58 岁,已婚,有六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我出生在拉斯艾因,一直住到 2019 年土耳其入侵我们的城镇。 我的第一次流离失所是到哈塞克,因为那里也不安全,所以我不能长时间待在那里,尤其是在爆发后来自拉卡和代尔祖尔的数十万流离失所者 (IDP) 来到这座城市之后叙利亚的战争。
哈塞克市曾经是该省的中心,曾经安全且井然有序,但在大量国内流离失所者涌入该市后,盗窃、抢劫、绑架和谋杀等犯罪活动增加了很多。
然后我在 2020 年搬到了 Qamishli,那里更安全、更好。 我是裁缝。 当我搬到卡米什利时,我租了一家商店,带着我的缝纫机和员工开始工作。 这是我的第二次流离失所。 我的大儿子也住在城里,其他人住在土耳其、库尔德斯坦、澳大利亚,最小的儿子在拉塔基亚学习医学。
当我搬到卡米什利时,我很高兴能感受到某种稳定,并且有很多朋友和客户。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的工作非常好。 我在卡米什利认识了很多人。 当我想起我的房子、大院子和镇上的大缝纫店时,我感到自己流离失所,但我仍然生活在我的国家,了解我与之交谈的人,文化并没有那么不同。 几乎是一样的。
我的大儿子正在卡米什利与新闻机构和人道主义组织合作。 我一直很担心我在卡米什利的大儿子和在拉塔基亚的小儿子,因为他们还在叙利亚,但我最担心的是我在卡米什利的大儿子,因为过去两年的情况并不安全,尤其是在许多孩子被蒙面人绑架,一些记者是我大儿子的朋友。
此外,财务状况和基本生活需求恶化。 在过去的两年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电力、燃料、水和面包。
除此之外,土耳其媒体的威胁一直存在,该地区的无人机袭击和爆炸以及每天都有许多人被任意拘留。
做出第三次流离失所并前往埃尔比勒的决定并不容易。 我们的生活就像一列火车,慢行,停在许多站台。 在我们停下的每一站,我们都认识了人、邻居、朋友……我们开始觉得我们住在这个站很舒服,但突然我们收到了来自后面的推动。 当你有一个长时间的休息时,再次这样做并不容易。 我们不是机器。 每一次休息和每一次新的飞行都会消耗我们的灵魂、情感和身体的很多东西。

我的大儿子几个月来一直试图说服我离开这个国家。 他告诉我,我们需要有护照和其他一些文件和文书工作。 我没有士气去做所有这些。 他正在为我准备一切。 他为我和他妈妈准备了护照文件,然后他买了去库尔德斯坦的签证,然后他买了机票。
我在卡米什利工作了两年,只能存 2000 美元(1700 英镑),而我的大儿子只能存 5000 美元。 我和他妈妈的两本护照,他和他的妻子和孩子的四本护照,每本护照花费 500 美元(总计 3,000 美元),而战前仅花费 20 美元,然后每个签证 250 美元(总计 1,500 美元),然后是居留在库尔德斯坦呆了一年,每人 600 美元(总共 2,500 美元),所以我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搬到了库尔德斯坦。
我记得当我们收拾行李前往卡米什利机场时,当飞机起飞时,我正从飞机的窗户望着这座城市。 我觉得我们是灵魂,祖国是身体。 当灵魂与肉体分离时,我感觉就像死了一样,但灵魂应该在天堂或天堂,但我们的灵魂在飞翔,却在受苦。
当我们在 2019 年被迫离开家乡时,我已经体验到了这种感觉,然后我们听说在我们找房子的时候,有人来自遥远的地方(代尔祖尔、古塔、阿勒颇)住在我们的房子里或住在帐篷里。 当我们在飞机上远离祖国时,我现在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相信土耳其人会入侵该地区剩余的城镇,他们的民兵会占领我们的房屋。 当你的伤口已经流血,而当这个伤口还没有愈合时,另一个刺伤同一伤口是非常困难的。
我和我的妻子、我大儿子的妻子和他的孩子(六岁和四岁)一起旅行。 大男孩问我,我们要去哪里,我回答他说,我们要和你叔叔的孩子一起去度假。 孩子们很高兴。 我希望他们在另一个国家长大,不要看到我们的灵魂和思想中存在的所有这些冲突和紧张。
当我们降落在大马士革时,我感到一丝希望,我们仍然在叙利亚,或者我们可能不会离开我们的祖国,但再次有从大马士革飞往埃尔比勒的航班。 伤口还在流血。 我们于 5 月 2 日傍晚降落在埃尔比勒。
我的儿子们来到机场迎接我们。 我现在在埃尔比勒,语言不同,我几乎听不懂埃尔比勒人说的库尔德方言(索拉尼语)。 这里的一切都不一样。 我需要几年时间来适应这个国家,但我们厌倦了流离失所。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流离失所。
母亲
我和丈夫花了 40 多年的时间来建造我们的房子。 我们家的每一件家具都有一个艰辛的故事,以及我们是如何购买它的。 当我在 2019 年离开家乡时,我非常难过并且生病了。 人们说它们只是物质,当你搬到另一个地方时,你可以购买其他的。 不,那些材料有灵魂、记忆和故事。 就连盘子、勺子、杯子,都有故事和回忆。
土耳其人正在占领我们的家园,并将其交给代尔祖尔和阿尔斯费拉的小偷、怪物和陌生人 [a town in Aleppo countryside where the Turish-backed Sultan Murad group came from] 他们只是因为他们是库尔德人而杀人。 我从来没有对几十年来一直是我们邻居和朋友的阿拉伯人怀有仇恨或敌意,但那些陌生人是不同的。 他们正在占领我们的房子。
我正在前往埃尔比勒和我的孩子们团聚,希望住在他们附近可以减轻流放和无家可归的痛苦。 我希望如果土耳其占领卡米什利,不会听到任何关于我们在那里的房子的消息。
儿媳妇
空手离开家,我感到非常难过和筋疲力尽。 我八年前结婚,我丈夫已经工作了大约 20 年,终于在四年前在卡米什利买了房子,去年买了车,现在我们把一切都抛在脑后。 该地区没有人会购买或出售房产,所以好像我丈夫已经工作了 20 年,将他所有的努力都提供给陌生人。
土耳其将来到我们地区,并将我们的房屋作为礼物送给陌生人。 我离开这个国家不仅因为土耳其人会入侵我们的城镇,还因为我的孩子们将在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土地上长大,这对他们来说并不安全。 在过去的两年里,有很多孩子被武装团体绑架。 我的一个亲戚去年失去了她大约 12 岁的儿子。他被武装团体绑架,至今失踪。
我的邻居几个月前也失去了她的女儿。 她 15 岁,有一天,一家人醒来并没有找到他们的女儿。 找她后,原来是被青年革命武装团伙带走 [a PKK-affiliated group conscripting children in northeast Syria]. 家人可以知道女儿在哪里,但武装团体拒绝送她,然后听说女孩被转移到伊拉克的甘迪尔山 [where the PKK are training their fighters].
每天早上我丈夫都会带我儿子去学校,下午他会带他回家。 我的小儿子有时想在我们楼下的街上玩,但我不能让他出去。 有男人开着大车从街上绑架孩子并卖掉他们的器官。 大约六个月前,我在 Derik 的一位亲戚在 Derik 失去了她 8 岁的儿子,后来她发现她的儿子已经死亡,被屠宰,器官被取走。 他的尸体在德里克镇附近的底格里斯河郊区被发现。
这就是我搬到埃尔比勒的原因,至少它比罗贾瓦更安全。
我一直担心我的孩子和丈夫。 大约八个月前,一个武装团体逮捕了一名记者,他是我丈夫的朋友,他被释放后,一些官员向他保证这是一个错误,但后来他又被逮捕并遭受酷刑,他的家人支付了很多钱让他自由。
儿子
我真的很累,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认为我的家人所说的解释了该地区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Source: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22/07/04/the-mass-ethnic-cleansing-of-syrian-kurds-is-collateral-damage-from-the-war-in-ukra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