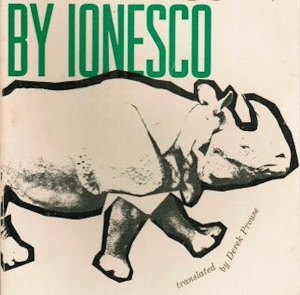迪伦·韦格拉
毕业后,我在韩国任教了六个月,然后搬到了亚利桑那州。 我在那里的第一年,他们想给我们加薪 1%,我认为这很荒谬。 我计算了一下,如果我每年加薪 1%,我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赚到 50,000 美元,这就好像我要等到教书 20 年后才能赚到 50,000 美元。 在一次学校董事会会议上谈到这件事后,我的一位同事说服我竞选工会执行委员会。 我只是把我的名字写在选票上就赢得了秘书选举。 我没有参加竞选,但参与度很低,足以赢得比赛。
西弗吉尼亚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老师在我第一个学期中期举行了罢工。 我最终被添加到一个有一群人的教师 Facebook 页面,但不久之后该页面的所有者将其关闭。 之后,我和工会的一些兄弟姐妹创建了我们自己的页面,亚利桑那教育工作者联合会,我们最终在这个小组中吸引了大约五万人。 我们开始建造类似于工会的结构。 我们有站点联络人,而不是传统的站点负责人,这是有意的。 我们使它与工会明显不同,因此教育工作者——其中相当一部分因工作权法而没有工会——会这样看待它。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广泛而包容的运动,包括那些没有缴纳工会会费的人,因为团结和人数更有力量。 我在该组织中的角色是作为现场联络协调员与其他几个人一起工作,支持学校的这些领导——与他们沟通、培训他们并帮助他们建立组织网络。
我成了群里的罢工者,不断推动我们罢工的人。 我对此直言不讳,不仅因为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策略,还因为我认为在一群人通过停止劳动而唤醒自己的力量中也有一些变革性的东西。 这是我认为我们在亚利桑那州真正需要的东西,即使只是为了向人们展示他们可以。 现在我搬回了密歇根,你仍然会听到很多人说,“好吧,罢工是违法的。” 我对此的回应是,“好吧,我们在亚利桑那州这样做是违法的,但我们还是这样做了。”
Source: jacobi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