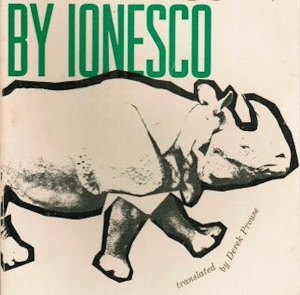共产主义会是什么样子? 反自由主义或至少是非自由主义似乎是右翼和左翼部分的共识。 前者担心社会主义者追求来之不易的自由; 后者怀有受 20 世纪早期启发的革命暴力幻想,认为自由主义只是政治变革的障碍。 这种对社会主义斗争中的利害关系的解释有助于在普通人眼中抹黑左派,他们听到谈论与自由主义决裂是一种加密威权主义。
他们是对的吗? 在 重温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重新思考正义、合法性和权利Igor Shoikhebrod 试图超越简单的问题,即作者是否 首都 是“支持或反对”自由主义。 比误导更糟糕的是,这种框架对我们的政治想象产生了有害影响。
舒伊赫布罗德认为,占主导地位的方法是将卡尔·马克思理解为拒绝自由的权利观念,因为它们预设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疏远和自私的个体”。 然后应该摒弃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念,因为它是“更丰富的人类自由概念的障碍”。 正确理解,共产主义超越了正义和权利,反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将其视为为统治阶级利益而进行资产阶级压迫的意识形态辩护。 无论共产主义最终是什么,它都消除了自由主义下法律的党派和个人主义性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替代方案。 在摆脱了稀缺性之后,共产主义社会将使私有财产权及其对法律制度的普遍影响变得不必要。
舒赫布罗德指出,事实上,马克思本人非常关心权利。 他积极支持扩大新闻和言论自由、政治权利、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权利等公民自由,并以法律约束资本和赋予劳动者权力。 在他的新闻工作和政治经济分析中,所有这些立场都是明确的。 德语中的权利, 法律, 马克思使用的具有其英语对应物的法律和道德内涵,但此外还唤起了我们共同的正义标准。 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些“永远不能高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以它为条件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比他的批评者想象的要聪明得多。 他承认权利在保护人们免受统治方面的价值,但他认为权利不能消除劳动对资本的依赖,这是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物质基础。 结束统治需要转变生产方式,而不是废除权利。
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认为我们受到组织生产关系的流行方式的限制。 因此,法律只能在这些关系上沉淀历史冲突的结果。 市场依赖,以及竞争对资本家施加的限制,对权利斗争的成果设定了严格的限制。 出于这些原因,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伦·梅克辛斯-伍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使政治权利更容易实现,同时又大大限制了它们。
马克思关于权利的立场源于他的观点,即我们可用的自由受到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统治形式的限制。 然而,这不应与否认权利相混淆。 那么,共产主义的合法性只会反映我们自由的不同物质基础,而不是兜售法庭放弃法治。
不幸的是,对马克思的主流解释排除了对权利的正确唯物主义理解。 讲英语的政治理论的元老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著名地宣称,马克思的想法是“超越正义的”。 在德国,Jürgen Habermas 尽可能地制定了限制资本的法律的规范性视野,同时向自由主义者承认,为了任何现代社会的协调目的,市场在功能上都是必要的。
最近,像 Axel Honneth 和 Nancy Fraser 这样的法兰克福学派人物也同样没有对资本主义以外的自由进行概念化。 相反,他们争辩说,它的市场有望实现尚未展开的历史自由(可能是向市场社会主义的演变),或者当代社会运动的进步派应该联合起来,将民主的范围扩大到经济。
这些方法都没有承认需要转变生产关系才能克服统治这一事实。 Shoikhebrod 提醒我们,重新谈判资本主义约束条件是不够的。
Shoikhebrod 的项目在抽象的哲学和实际的政治层面都有利害关系。 如果我们接受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截然相反的主流观点,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将使资本主义社会变得宜居的自由自由归功于资本主义,而不是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
由欧洲和美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引发的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思考由来已久。 在这个故事中,资本家是一个革命阶级,他们推翻了基于种族、性别和其他先天性等级制度的封建财产关系和前现代形式的统治。 他们为推翻和反对拥有土地的贵族而进行的私有财产权斗争在推翻旧制度方面发挥了本质上的进步作用。
因此,资本主义本身在道德上是进步的,马克思自己对此的评论支持了这一观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解放穷人、妇女和工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机会。 他认为,资产阶级权利是一种工具,必须用于结束其自身的取代。
马克思因假设资本主义是进步的而受到广泛批评,批评者声称,这一观点是他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证据。 这些批评者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导致到处都出现自由主义。 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理论家错误地预测了欧洲在世界范围内的经验,忽略了资本主义与奴隶制或殖民统治的相容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指出资本主义和非自由主义并存的马克思的批评者坚持认为,该制度 曾是 实际上在欧洲是进步的,但不是在欧洲之外。 这种观点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即权利不仅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而且特别是欧洲资产阶级的产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信念本身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它否认工人阶级的能动性,并忽视了为自由改革而进行的底层斗争。
如果马克思错了,那是因为他更基本的假设是资产阶级永远是进步的,即使在欧洲也是如此。 相反,工人阶级、穷人和农民为了最基本的政治权利而争相登上政治舞台,采用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策略,迫使资本家动不动就让步。 的确,资本和资产阶级不是一回事。
许多早期的资本家实际上是向依赖市场的农业生产转型的老地主。 他们为压制民主改革进行了恶毒的斗争,而且往往是这样做的最积极的力量。 没有理由将任何对资产阶级权利和正义的特别渴望归因于他们的阶级利益或道德世界观。 使资本主义与世界各地不同程度的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相容的原因在于它与自由主义自由是分不开的。
马克思 和 他的批评者对资本主义过于慷慨。 他们将劳动负责的社会进步归功于该系统。 资产阶级权利属于资产阶级的观点为左翼观点提供了保证,即权利的存在只是为了证明经济统治是正当的。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它忽略了那些对自由权利真正有价值的人:为扩张而进行政治斗争的工人,他们对这些权利的承诺使资本主义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 他们的胜利不是不可避免的,减少他们的收益也不是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政治与资产阶级政治即自由主义的区别,不在于种类的区别,而在于视角的区别。 自由政治管理统治; 社会主义政治试图废除它。 因此,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本质上并不是法外的或超越正义的。 相反,其战略和优先事项的道德合法性来自超越统治的人类自由理想。
在上个世纪,社会主义者大肆批评苏联的实验,并认为它的问题在于它忽视了公民自由和宪法权利。 就其本身而言,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 它正确地指出了国家共产主义的经济主义或生产主义的问题。 然而,这导致许多人争辩说,关于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太多,而关于政治的理论还不够。
然而,Shoikhebrod 的论点表明,社会主义者对两者的思考都太少了。 社会主义的未来将有权利的物质基础,就像现在的资本主义一样,但这些权利将以自由为基础。 社会主义者应该搞清楚这会是什么样子。
Shoikhebrod 著作的优势在于,他承认经济自由与法律自由之间的关系,表明前者对后者施加了限制。 这种观点的转变使我们能够质疑西方资本主义坚持为自由自由授予制度信用的捍卫者。 在西方,反共主义实际上成功地将自由本土化,将其目的描绘为资本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左派经常同意这种偏见。 这是一个不需要做出的让步,因为资本主义下的自由承诺是资本本身没有做出的。 对于这个承诺,自由主义者可以感谢社会主义者,因为自由一直是我们项目的核心。
Source: jacobin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