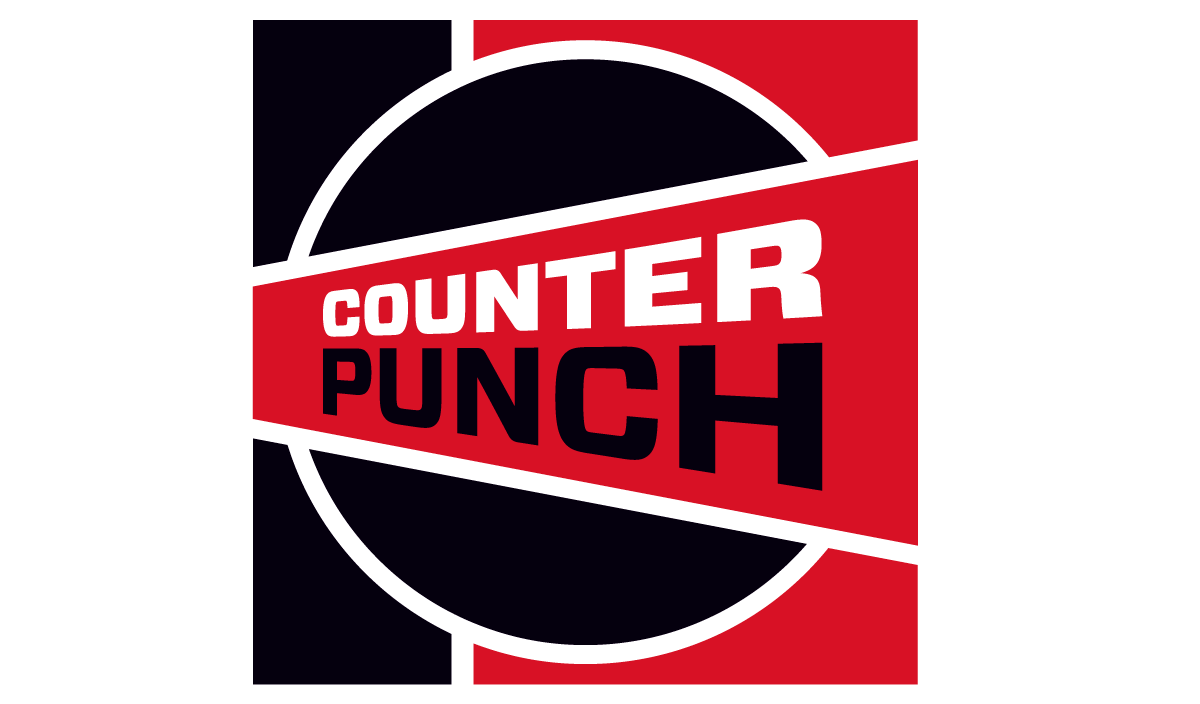
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精神上的、精神上的、身体上的。 我在 16 岁时宣布自己不信奉父母的宗教。我刚读过这本书 出埃及记,由莱昂·乌里斯(Leon Uris)撰写,并且不能容忍教会的教导,即所有非信徒,包括所有犹太人,都会下地狱。
再见,星期天的教堂。 我妈妈很伤心,但我们慢慢地和好了。 那年夏天,在一个家庭度假时,当我们在芝加哥高架公路上行驶时,收音机宣布了龙卷风警告。 妈妈后来写了一篇发表的文章,结尾是这样的:“三个基督徒和一个不可知论者祈祷。”
换句话说,我们找到了一个超越生活文化确定性的空间来重新连接。 我们彼此相爱;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超越了所有宣称的宗教确定性。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探索这个领域——你可能会说,伟大的彼岸。 我在高中写的最后一篇论文,我的“高级论文”,标题是“男人的思想是他自己的吗?” 我的主要参考资料是乔治奥威尔的 一九八四 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 美丽新世界. 是的,我决定,直视老大哥那目瞪口呆的眼睛,我是我相信什么,我看重什么的最终决定者。
这并不意味着事情很容易——恰恰相反。 这是 60 年代中期。 社会变革开始渗透,而我大多天真,大多与美国白人同步:当时的现状。 与其说我相信它,不如说我只是慢慢地注意到它。 我的父母是艾森豪威尔共和党人。 在 1960 年的选举中,我一直非常支持尼克松。 但是民权运动开始渗透到我读到的新闻中(除了体育版,这并不多)。 嗯。 我站在哪里?
当我拖着脚步上大学时,越南战争正在加速。 作为一名大学生,是的,我没有参加选秀,但我主要关注的是个人事务:哎呀,微积分! 我将从事什么职业? 那个在食堂上班的妹子好漂亮啊! 但更大的世界确实开始慢慢渗透到我的意识中。 我参加了关于战争的正式的、教授性的辩论。 我也在大二结束时决定停止剪头发。
到 1967 年,我搬出了校园——这是第一次! 本质上,我刚刚进入——看起来如此——一个平行宇宙,它正在建设中。 我可能是创造者之一。 大麻? 好的,我试试看。 我还记得第一次抽大麻。 我会变高吗? 突然间我饿了。 我们做了吐司,涂上黄油,然后,哦,我记得很清楚,我开始撒葡萄冻,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葡萄果冻的宝石! 这太不可思议了。 然后,那年秋天,我和一群朋友去了五角大楼的第一次游行。
一切都是有联系的,对吧? 我记得我漫步在五角大楼的场地上,突然一群士兵向我们冲来。 我被枪托击中头部。 啊,我的红色勇气徽章。 我和我的朋友最终决定不被捕。 我们步行回到我们住的那个人的公寓,第二天开车回密歇根。 然后我辍学了。
人的心是自己的吗? 是的,当然,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这是 60 年代后期,嬉皮士正在改变世界。 我现在很容易受到选秀的影响,但我不在乎。 我有更大的事情要处理,比如在我的大众巴士侧面画一首圣经诗句:“让一天的烦恼足以应付一天。”
是的,这是我当时的错觉。 我以为我参与了创造,你知道,和平。 我们一群人开车穿越全国到旧金山——当然是到海特。 但最终军队开始追赶我,我最终搭便车回到了我的大学城卡拉马祖,在那里我寻求了一名征兵顾问(和朋友)的帮助。 事情变得相当奇怪。 在她的建议下,我写了一封信给我当地的选秀委员会,要求亲自拜访,并获得了批准。 我所做的是写了一段长的人生哲学,主要是引用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 我宣布我是拉斯科尔尼科夫。 选秀委员会的人告诉我,我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而不是因为我的信仰而被捕入狱,我最终得到了 2-S,暂时延期。 当时我松了口气,但后来开始感到内疚——不是我没有参军,没有受过基础训练,然后去杀了一些越南人,而是我没有采取明确、明确的立场,没有忍受结果。 迫在眉睫的,我开始理解,是这个男子气概的事情。 有些线需要跨越。 我能感觉到这种需要。
多年来,我一直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 我回到学校,拿到了学士学位(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开始以某些方式改变我的信仰体系——例如,我开始定期洗碗。 我找到工作粉刷房子,开出租车。 最终,我在一家小镇报社找到了一份工作。 换句话说,我开始长大了。 我结婚了。 但我仍然感到一种模糊的、迫在眉睫的需要。 . .
什么?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世人,因为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与年轻男性枪支暴力等问题有关,更不用说正在进行的战争了。 有一种痛苦的男性需要从童年走向成年,不是以某种平淡无奇、自动的方式(你知道,变老),而是有目的、有坚定的信念和努力。
在我生命中的这一点上,环境运动已经获得了文化基础,随着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妇女权利运动而出现。 我是一个大城市的男孩,但我和我的妻子感到被环保主义吸引了。 我没有所需的技能,但我致力于学习。 我现在以前的大学的一位宗教教授,他是一个南达科他州的农场男孩,他创办了一个他称之为宅基地的学校。 我和我的妻子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年。
这是在密歇根西南部的农村,那里的冬天通常很苦。 我们住的小房子只有一个柴火炉作为它的热源。 我砍了木头。 这是我的选择,感觉非常正确。 一月二月三月 。 . .
我们度过了冬天——四个中的第一个——靠木头加热。 我决定这是我成年的通道。 我自己选的。
Source: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22/07/04/growing-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