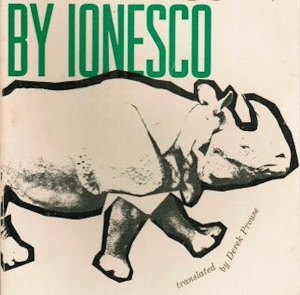继法国最近针对养老金改革的罢工和示威之后, 克莱门特穆奥 写了法国最近一波抗议浪潮的起因。
在 2019-2020 年的一次失败尝试之后,马克龙和他的政府终于回到了第二个总统任期似乎唯一真正的目标:增加工人在领取全额养老金之前必须工作的年数。 在法国的养老金制度中,全额养老金需要满足两个条件:最低工作年限(现在 1973 年之后出生的人为 43 年)和最低年龄(现在为 62 岁)。 通过过去二十年的几次改革,这两个门槛有所提高。 马克龙的计划是将最低年龄提高到 64 岁,并建议未来进一步提高。 与此同时,平均预期寿命极不平等。 从事白领工作的人平均比蓝领工人晚死 6 年,但这个数字只是暗示了更严重的不平等:白领专业人员的平均无残疾预期寿命比蓝领长 10 年。 从事对体力要求最高的工作的人也是那些开始工作时间较早、没有受过太多高等教育以及在晚年面临失业最多的人。 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和管理人员几乎不受法律变化的影响,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学习到 23 岁或更晚,而养老金规定要求的工作年限意味着他们已经必须工作超过 64 岁。这种公然的不公平并没有被忽视:政府已经向下层阶级宣战,与男性相比,工人阶级女性受到拟议改革的负面影响更大。
但仅凭这项改革并不能解释愤怒的程度。 环境在很多方面与英格兰相似,同样的原因在海峡两岸产生了同样的效果。 除了非常特权的阶级之外,每个人都熟悉这些原因。 几十年来,由于通货膨胀导致的年度减薪一直在侵蚀工资,并且在过去两年中随着基本商品和供暖价格的爆炸式增长而残酷地加速。 然后是对所有提供公共服务或依赖公共服务的人的政治和媒体骚扰:护士、教师、邮政工人、养老金领取者、残疾人、社会住房租户等。 来自所有主流政党的政客们一直在不懈地推动改革,以削减对医疗、养老金、学校、住房的资金——所有这些都能给那些并非天生富有的人的生活带来尊严。 税收对公共服务的再分配资金大部分流向了市场。 在这里,就像在法国一样,左翼和右翼政府都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减少国民财富中用于再分配的比例,或者换句话说,这是社会化的,从而摆脱了利润逻辑。
与英国不同,在法国,人们对养老金改革的愤怒直指国家层面,因为养老金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国家和国家组织的。 最近的运动并非突然发生。 如果没有 1995 年 12 月的红色冬天,它就不会存在,当时工人阶级提醒 Juppé 的傲慢政府它仍然是所有劳动力的来源,并通过公共交通工人罢工和群众示威相结合来阻止养老金改革,压倒性的公众支持。 在这个红色冬天之后,2003 年、2010 年和 2019-2020 年又发生了其他群众运动,再次反对试图减少养老金数额和期限的养老金改革。 连同 2006 年和 2016 年反对劳动力临时化改革的两次群众运动,这些群众运动拒绝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人支持这些运动。 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国和英国,即使是最保守的政治家也不再将选举宣传的重点放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上; instead, they focus on racist or nationalist issues to continue winning elections.
最近两天的集体行动,即 1 月 19 日和 31 日,见证了法国社会历史上一些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Read more about these strike days in an interview with a worker here.] 事实上,政府 1 月 31 日的官方数字是全国 127.2 万人,这是自 1990 年代引入系统计数以来有记录以来的最大示威人数。 比1995年12月和2010年11月高峰时的人数还要多,是1995年12月运动开始时示威人数的两倍。也许更惊人的是,中期记录的历史数字——大城镇和小城镇,经常发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这绝对不是一场仅限于城市知识分子中心的运动,而是一场深深植根于社会各阶层的运动,尤其是在体力劳动者和外围地区。 民意调查证实了这一点,显示超过70%的人支持运动并反对改革。 当民意调查仅限于劳动人口时,高达 93% 的人反对马克龙的改革。
在本周的示威游行中,绝对有一种重逢的幸福感,一种集体力量感,一种打破主流媒体持续不断的反工人话语的喜悦。 正如作家安妮·厄诺 (Annie Ernaux) 最近写在 Le Monde Diplomatique,又像1995年那样,有“抬头”的感觉。但与1960、70、80年代的社会运动不同,它夹杂着近乎务实和悲观的决心。 政治和经济统治者显然已经停止与社会运动玩“谈判游戏”,妥协或胜利与示威游行和公众支持的规模成正比。 这些统治者早已放弃了为其新自由主义改革赢得多数支持的任何希望,因此他们刚刚学会了忽视、耗尽或诽谤反对派运动,或者通过诉诸种族主义言论来转移注意力(本周,马克龙提出了一项新法案反对难民和移民)。 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削弱了工会、协会和政党中的代表和官僚的中间层,因为他们没有太多的谈判能力来满足他们的普通民众。
因此,群众运动一直在寻找获胜策略。 1995 年 12 月的策略是将一小部分受到更好保护的有权势工人(运输工人)的无限期罢工与群众示威和受保护较少的工人偶尔举行的一日罢工结合起来,同时进行一场赢得公众的坚决斗争观点。 但政治家和机构媒体已经学会了反击这种策略。 最近,黄夹克 (gilets jaunes) 运动通过长期定期占用公共空间来进行常规破坏。 一些更激进的政治阶层和工会活动家主张将总罢工作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但这并没有解决如何达到所需的协调水平和罢工承诺以发生这样的总罢工的问题,过度随意和支离破碎的社会。 尽管如此,运动的每一波浪潮都为工会和政治活动家带来了新的经验、新的想法和新的信心。 这种对获胜策略的探索已经导致了许多有价值的普通民主传统,降低了工会官僚瓦解运动士气的能力。 这些包括大会和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
自 1995 年以来,两个部门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炼油厂的工人——由法国最大的工会 CGT 组织——以及高中和大学生,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协调示威和罢工与学校和大学的占领校园。 它们可能是当前运动结果的关键。
Source: www.rs21.org.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