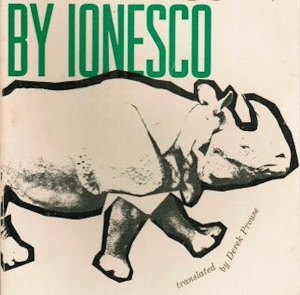在我们对互联网的实验几十年后,我们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它实现的连接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形式的交互无疑带来了好处。 人们可以更轻松地与他们所爱的人交流,获取知识以使自己保持知情或娱乐,并找到无数原本可能无法企及的新机会。
但是如果你今天问人们,对于所有这些积极的属性,他们也可能会告诉你互联网有几个大问题。 呼吁“拆分大科技”的新布兰代斯运动会说,问题在于垄断以及主要科技公司因此而积累的权力。 其他激进分子可能将问题描述为公司或国家使用这种数字基础设施提供的新工具侵犯我们的隐私或限制我们自由表达自己的能力的能力。 根据问题的定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声称可以控制这些不良行为,并让公司接受更合乎道德的数字资本主义。
这些活动家的主张肯定有一些道理,他们提议的改革的各个方面可能会对我们的在线体验产生重要影响。 但在他的新书中 互联网为人民:为我们的数字未来而战, Ben Tarnoff 认为这些批评未能确定互联网的真正问题。 垄断、监视和许多其他问题是系统中更深层次缺陷的产物。
“根源很简单,”塔诺夫写道:“互联网已经崩溃,因为互联网是一门生意。”
互联网为人民 带领读者穿越互联网的历史及其问题。 但塔诺夫分析的核心是私有化问题:私有化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对几乎不可避免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产生了什么后果。
这本书带我们经历了互联网发展的一系列关键时刻:1969 年,公有的高级研究计划署网络 (ARPANET),第一个成为互联网先驱的公共计算机网络,首次上线时间; 1976 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 首次将两个网络连接起来,以实现“将大型机推向战场”的目标; 1983 年,当 ARPANET 切换到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协议 (TCP/IP) 时,互联网和各种计算机网络中使用的通信协议是现代互联网的基础; 1986 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启动了 NSFNET(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网络),这是一个国家公共骨干网络,允许更多人(尤其是研究人员)使用它进行通信。
在每个阶段,Tarnoff 解释了为什么政府对于允许这些发展以私营部门无法实现的方式发生至关重要,并接受“开源伦理”,这与“将用户锁定在专有网络中的商业冲动”背道而驰。系统。”
以允许这些不同网络相互通信并最终产生 TCP/IP 的协议为例。 “在私有制下,永远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语言,”塔诺夫写道。 基础研究工作不仅非常昂贵,而且没有明显的方法可以从中获利。 事实上,DARPA 甚至为 AT&T 提供了接管 ARPANET 的机会。 AT&T 拒绝; 它看不到可行的商业模式。
在所有这些投资之后,互联网在 1990 年代经历了彻底的转变。 对 Tarnoff 来说,那是“互联网突然死去,又出现了一个不同的互联网”的十年。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上网,企业终于开始从中看到赚钱的机会,但 NSFNET 的可接受使用政策禁止商业活动。 在新自由主义霸权时代,这是站不住脚的。
不管互联网的全球潜力如何,有关其治理的决定都将在华盛顿特区做出。 在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的共和党和比尔·克林顿总统的民主党中,前进的道路很明确:互联网必须私有化。
决定性的日期是 1995 年 4 月 30 日。互联网的公共主干网络国家科学基金会网络 (NSFNET) 被关闭,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方面让给了私营公司。 塔尔诺夫将这一事件描述为行业规定的“错误选择”的产物,其中选择被框定为“将系统作为受限制的研究网络或使其成为完全私有化的大众媒体”。 在通过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广泛议程赋予“市场”信任的时刻,商业和政治精英希望我们相信没有其他选择。
尽管 1995 年可以被视为私有化的时刻,但 Tarnoff 将其定位为一个进程的开始,该进程从互联网管道私有化开始,然后借助行业自己的术语进入“堆栈”。 毫不奇怪,克林顿政府和 1990 年代中期的其他权力人物认为私有化是实现更好的互联网的唯一途径,这是一种更便宜的访问并刺激创新的途径。 然而,私有化的结果却完全不同。
美国现在为一些最糟糕的互联网服务支付了世界上最高的价格,因为放松管制和整合的电信寡头垄断控制了大多数人的访问。 与此同时,现代科技垄断企业——Facebook、谷歌、微软和亚马逊等公司——正在大力推进互联网的基础设施领域,因为他们购买了更多连接世界的海底电缆。 Tarnoff 认为,当他们建立“垂直整合的帝国来控制管道和其中的信息时,他们正在将 1990 年代重建的互联网重塑为更加私有化的形式。”
万维网的重新定位以服务于这些公司的业务需求而不是其用户是这个等式的另一面。 互联网热潮正是这一过程开始的时刻,因为新公司正在寻求从我们在网上所做的事情中获取利润的方法。 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们经常将这些公司提供的服务称为“平台”,但这是 Tarnoff 拒绝的术语。 它使他们能够“呈现出开放和中立的光环”——当他们实际上正在塑造我们为他们的利益所做的事情时。 塔诺夫将它们称为在线商城,即看似公共的私人空间,我们聚集在一起,为控制它的公司创造利润。
Tarnoff 熟练地描绘了这一推动私有化的过程是如何展开的,他着眼于 eBay、谷歌和亚马逊等关键公司在不同阶段为建立在线商城模型、扩展云基础设施、转变过程所做的贡献将数据制作变成一项有利可图的业务,并将互联网从家庭或办公桌推向社会的许多方面。
这些发展没有实现 1990 年代的自由主义乌托邦梦想,反而产生了可怕的影响:为剥削边缘化人群提供了新的手段,促成了新一波的右翼激进化,并帮助创造了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源:私有化的互联网让我们失望了。
虽然隐私立法和反垄断措施可能会产生一些积极影响,但还远远不够。 塔诺夫写道:“私有化的互联网将永远等同于少数人的多数统治,”而且由于这种趋势已经根植于资本主义本身——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某种迭代——修复互联网需要一种不同的策略:剥夺。 但它看起来像什么仍有待商榷。
塔诺夫没有为一个被剥夺的互联网制定具体计划,而是解释说实验将是关键。 他设想的未来是技术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它从“完成的事情 至 人,并成为他们一起做的事情。” 与其坐等谷歌或亚马逊给我们什么,技术是由社区和集体生产的,以满足非常不同的需求和目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塔诺夫没有给我们留下我们可以采取的路径的地图。
在基础设施方面,塔诺夫明显偏爱社区拥有的网络,这些网络已经在美国扩散开来,尽管它们面临电信寡头垄断的反对。 这些网络倾向于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服务,同时优先考虑社区需求而不是大公司股东的需求。
同时,在服务方面,塔诺夫瞄准了“大”,因为他们需要为自治所创造的困难和他们促进的负面社会互动产生回报。 相反,他提出了一种“协议化”社交媒体模型,其中包含可以相互互动的小社区的扩散,并且公共资金可用于媒体。
尽管始终未能实现这些雄心壮志,但互联网长期以来一直被自由主义理想主义所包围,并且许多关于更好的互联网的想法都倾向于去中心化。 由于 Tarnoff 依靠现有的想法来概述被剥夺的互联网如何运作,因此他的愿景也可以被视为具有其中的一些品质。 然而,在他对社区网络的讨论中,他指出去中心化并不是一种固有的好处,因为它可以被一些数字权利活动家和技术自由主义者定位。
“权力下放并不是天生的民主化:它可以像分配权力一样容易地集中权力,”他写道。
最终,私有化的互联网将需要针对网络不同方面的不同解决方案。 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会表现出对权力下放的偏好,而在其他情况下,则需要采用区域或国家方法。
正如塔诺夫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告诉我的那样,“你不能完全分散互联网,也不能完全集中互联网。 问题总是:你想去中心化什么,你想去中心化什么?”
通过重新构建关于互联网的辩论,而不是围绕监视、言论或垄断,而是围绕更深层次和更基本的私有化过程, 互联网为人民 鼓励我们更广泛地思考不同类型的互联网如何运作以及它可以为谁服务。 在科技行业的未来似乎比最近记忆中的时间更受质疑的时刻,这是我们迫切需要进行的对话。
Source: jacobi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