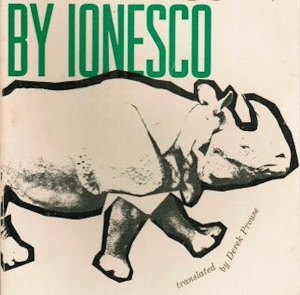自由党自 1946 年成立以来,一直是澳大利亚统治阶级的政治喉舌。 联邦选举摧毁了其选举中心的大部分地区,并使该党作为一个统一实体的未来受到质疑。 在一个又一个城市,自由党(以及他们的保守派前辈)占据了几十年的席位落到了他们的对手手中。
在珀斯,该党失去了五个席位,四个席位输给了工党,一个席位输给了独立党,现在该党在该市的八个席位中只占据了两个席位,两党的波动幅度为 10-15 个百分点。 在布里斯班,工党和绿党拿下两个席位,而在阿德莱德,工党拿下一个。
悉尼和墨尔本的失利可能会被证明是自由党最难恢复的,因为在这里自由党的基础最明显地分裂了。
在墨尔本,自由党失去了 4 个席位,其中包括最蓝的 Kooyong 席位,两党以 10 分的优势击败联邦财长 Josh Frydenberg。 自 1901 年成立以来,Kooyong 只认识保守派代表,包括自由党创始人和长期担任总理的罗伯特·孟席斯和前自由党领袖安德鲁·皮科克。
由蒂姆·威尔逊(Tim Wilson)持有的戈德斯坦(Goldstein)覆盖墨尔本内东南部的布莱顿和桑德灵厄姆(Sandringham),这是自由党在另一场两党首选的10分波动中的又一次失利。 自 1984 年成立以来,这一直是自由党的领地。墨尔本这些损失和其他损失的结果是,自由党在 CBD 25 公里范围内没有任何议员。
在悉尼,两党偏好的 5 到 15 点之间的波动导致自由党在富裕的东郊、北岸和北海滩失去 5 个席位。
该国最富有的选民温特沃斯(Wentworth)自联邦成立以来几乎没有中断,由保守派控制,投票否决了自由党现任戴夫夏尔马。 就在北悉尼的海港上空,特伦特齐默尔曼失去了一个传统上非常安全的自由党席位,这是仅有的两个席位之一——连同温特沃斯——从来没有被工党占据过。
在北部海滩,两任自由党现任议员 Jason Falinski 失去了 Mackellar,这是自由党在其 73 年历史中只有两个月的席位,而独立的 Zali Steggall 则保住了 Warringah,这是她在 2019 年从 Tony Abbott 手中夺取的席位。自由党现在在悉尼盆地地区的 26 个席位中只占据了 7 个席位,全部位于最北郊、南郊和西部偏远的彭里斯。
正是在悉尼和墨尔本,蓝绿色的独立人士充分利用了自由党的失败(Warringah、Kooyong、Mackellar、North Sydney、Goldstein 和 Wentworth)。 在珀斯富裕的海滨西郊,另一位独立人士凯特·钱尼(Kate Chaney)在科廷(Curtin)取得了同样的成就,自由党几乎在其存在了 70 年的时间里一直占据着这个席位。
由于几个原因,这些结果给自由党带来了灾难。 首先,失去这些腹地席位使他们更难赢得下届选举。 其中一部分是纯粹的算术。 由于联盟党可能只持有 59 个席位,要想在 2025 年获得组成多数政府所需的 76 个席位,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是在 2007 年,当霍华德政府被陆克文的工党扫地出门时党,失去22个席位,联盟党仍保住65个席位。 自由党和国民党现在只持有该国 45 个内陆大都市席位中的四个。 这不仅仅是一个联邦问题; 新南威尔士州自由党政府很可能在明年三月的州选举中面临类似的挑战。
虽然在与蓝绿色的竞争中,自由党的两党支持率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低于 46%,使他们距离重新夺回这些席位有惊人的距离,但像 Steggall 和沃东加的独立人士海伦·海恩斯这样的独立人士的经历,他现在以 60% 的两党首选票数保住自己的席位,是独立人士可以在随后的选举中巩固和增加他们的优势,并且很难被赶下台。
独立派的成功撕裂了自由党内右派和所谓温和派之间的分歧。
The right has been making ground since the election of the Howard government in 1996. Howard and his allies did much to destroy what were then called the party’s “wets”. 霍华德可能在 2007 年落选,但在 2013 年赢得政府的托尼·阿博特 (Tony Abbott) 进行了类似的极右翼议程。 Supposed moderate leader Malcolm Turnbull hedged his bets, and Morrison’s election as leader in 2018 confirmed the ascendancy of the right. 结果是一个社会反动的议会核心小组,反映了广大党员的偏见。 他们得到了新闻集团小报的支持, 澳大利亚人 报纸、天空新闻和资源部门的资本家。
蓝绿色独立人士的成功部分是传统自由党选民对该党社会反动议程的反抗,特别是其性别歧视、对环境措施的敌意以及对议会程序的公然蔑视。
达顿领导的政党将很难有效应对大城市富裕地区传统中心地带的丧失。 在凶猛的新闻集团运动的鼓励下,右翼推动的一个选择是放弃他们,将党集中在更遥远的郊区、城郊地区、区域城镇和农村选民,推动一项旨在在“有抱负的选民”和社会反动派。
达顿表示,他不会让该党走上这条路,并将把它维持为一个“广泛的教会”,有温和派和正确的合作。 然而,鉴于他作为右翼头号人物的全部记录,以及需要将自由党与工党政府区分开来,并保护该党的右翼免受一国党和 UAP 之类的攻击,达顿不太可能抵制推动党向右。
然而,这样做的问题在于,它几乎没有机会赢得足够的席位来组建政府。 澳大利亚的选举在六个首府城市中获胜和失败,其中包括纽卡斯尔、卧龙岗、吉朗和阳光海岸和黄金海岸等附近城市以及堪培拉,这些城市占据了大部分席位。
没有像美国那样偏远的中型城镇中政治生活由共和党人主导的大量席位或选举团选民,也没有使这些保守地区政治代表性过大的倾斜选举制度。 在农村地区,自由党和国民党已经占据了 38 个席位中的 29 个,这让他们几乎没有机会在那里取得很大的增长。
尽管如此,自由党可以通过将自己重新定位在极右翼来应对失败的前景应该引起左翼的关注。 由达顿领导的右翼特朗普政党可能会吸引极右翼,在这次选举中,极右翼赢得了大约 12% 的全国选票。 国民队多年来经历了极右翼的渗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它。 一个更明显的右翼联盟未来可能会选择不这样做。 自由党的新南威尔士分支几十年来一直有大量右翼存在(“丑陋”),而在维多利亚,右翼福音派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展,因此党内有现成的听众极右翼的推动。
自由党能否向另一个方向倾斜以赢得蓝绿色席位? 很难看出谁能带领该党朝这个方向发展。 达顿是最后一个站着的人,至少除非该党将现任议员推到一边,以便在未来几个月的补选中为弗莱登伯格创造一席之地。 几十年来一直在排挤温和派的右派也不可能希望通过让温和派候选人坐在蓝绿色座位上来给他们一条生命线。
蓝绿色可能会因为过于接近可能成为不受欢迎的工党政府而毁灭自己,从而为自由党在下次选举中接手他们创造空间。 但考虑到蓝绿色大部分是为了市场“解决方案”和“税改”,而不是工会的朋友,这似乎不太可能。
最后,如果自由党历来是统治阶级的喉舌,那么其队伍中的危机就会给资本家带来麻烦。
自由党不仅是议会政党,也是凝聚统治阶级的重要组织。 一个多世纪以来,自由党和民族党代表资本与工人阶级进行了政治斗争,使资本家得以继续在生产环节剥削工人阶级的日常工作。 它们还为资本的竞争部分提供了一种进行辩论的方式,而无需参与可能为工人阶级发展其命运提供机会的公开斗争。
统治阶级重视自由党和国家党,并通过多种方式支持他们,包括大众媒体、捐赠、赞助公共事务研究所等政党智库、释放工作人员参与竞选活动以及作为资本家在惠特拉姆工党政府执政的最后一年,他们通过投资罢工和资本外逃对对手进行金融破坏。
这并不是说统治阶级一直反对工党赢得多数。 1983 年,统治阶级支持鲍勃·霍克(Bob Hawke)的工党赢得公职,因为事实证明弗雷泽政府如此无能,而霍克提出了一个驯服工会和削减工资的计划,他在 1980 年代做得非常成功。 在这次选举中,这就是艾博年的自由主义议程,大多数统治阶级并没有支持莫里森,明显的例外是新闻集团。 但工党是 B 队; 自由党是统治阶级最喜欢的工具,因为它不受工会的影响,即使是工党通过其内部结构和政治吸引力以最卑鄙和腐败的方式。
在许多情况下,蓝绿色与他们击败的自由党来自同一社会环境,他们的胜利代表了统治阶级队伍的分裂。
Tally Room 博客的 Ben Raue 的分析表明,由蓝绿色赢得席位的选民拥有最高的收入中位数和最高的教育资格。 尽管正如民意测验专家科斯·萨马拉斯(Kos Samaras)所指出的那样,高收入中位数掩盖了悉尼温特沃斯邦迪等地区许多低收入学生和酒店工作者的存在,但这些席位一直是自由党运作的核心,也是许多自由党的所在地。企业和个人的主要人物和财务支持者。 所有将统治阶级联系在一起的顶级私立学校、豪宅、社交网络都位于这些地区。
蓝绿色的胜利和自由党在其传统中心地带的打击表明这些精英的裂痕。
温特沃斯的胜利者阿莱格拉·斯彭德是一位来自强大自由党家庭背景的商人——她的父亲是自由党议员,祖父是孟席斯政府内阁部长珀西·斯彭德爵士。 凯特·钱尼(Kate Chaney)是前 Wesfarmers 高管,是孟席斯政府部长的孙女和前自由党参议员的侄女。 其他人有大律师、儿科神经科医生、公共关系专家和全科医生的背景。
蓝绿色的运动是由澳大利亚第一位亿万富翁罗伯特·霍尔姆斯·考特之子西蒙·霍姆斯·考特管理的气候 200 组织协调的,他早些时候曾为弗莱登伯格筹集资金。 气候 200 得到了 Atlassian 软件的亿万富翁创始人 Mike Cannon-Brookes 和拥有 Sussan 和 Sportsgirl 的 Nancy Milgrom 的支持。 董事会成员包括前自由党议员 Julia Banks 和前自由党领袖 John Hewson。
蓝绿色得到了自由党的支持,如 Rob Baillieu,来自墨尔本的一个长期建制家庭,也是前维多利亚州自由党总理 Ted Baillieu 的儿子。
这些都是自由党的东西,但已经开启了“他们的”政党。 并且不排除蓝绿色可以组建自己的政党,如果他们能够在几次联邦选举中巩固它,可能会成为联盟党凭借自己的权利赢得职位的一大障碍。
Source: https://redflag.org.au/article/liberal-party-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