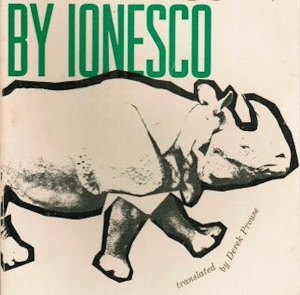给
我于 2016 年开始为 Uber 开车。Uber 提供了很多激励措施,包括 1,000 美元来支付您的初始成本,因为当然,即使是起步,司机也要负责我们工作所需的设备,即车辆。 走出大门,我不得不自掏腰包 700 美元来获得出租车和豪华轿车委员会的执照、课程和培训。 我以每周 450 美元的价格租了一辆 2015 年的现代索纳塔,行驶里程超过 8 万英里。
开车很困难,尤其是在开始的时候。 我辛勤工作只是为了还清租车所需的 450 美元。 我与租赁公司达成了一项安排,他们会从我的工资中扣除钱,然后我什至可以在周末使用它们。 很多时候,在交完油费和其他费用后,如果我想有零花钱,我就需要加班。 有时候,我刚开始开车时,我是在亏本经营的。 我与优步的余额为负数。 最终,我得到了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买了一辆车,我预付了 2200 美元。 虽然比租车便宜,但考虑到我当时的信用不佳,车费仍然过高。
我喜欢开车和与人交流,但我讨厌疯狂的时间。 我经常不得不睡在车里,因为我太累了,无法安全回家,或者因为我还没有赚到足够的钱。 我经常在机场打盹,而在两次旅行之间打开应用程序。
当我刚开始开车时,尽管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司机通过航站楼,但机场甚至连卫生间都没有。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安装便携式便盆时的兴奋。 但是,满足基本需求(例如在工作中使用洗手间)不应该是一种了不起的体验。 我研究了一个帮助赢得厕所使用权并开始支付会费的组织之一。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参与了一些行动,以反击该市为规范该行业而采取的一些倒退措施,这些措施为已经负担过重且工资过低的司机增加了额外费用。 最终我们关闭了布鲁克林大桥,要求提供更好的补偿。 我们看到拼车公司不断削减工资、工时和可达性,而他们的高管却获得了创纪录的利润。 随着市场每天充斥着更多的司机,我们要求并赢得了该国独立承包商的第一个薪酬底线。
但即使这样还不够。 我花了更多时间代表司机组织互助——让他们获得资源,让他们获得 PPE 贷款,帮助他们驾驭系统——而不是开车。
我曾在一个名为 United for Brownsville 的组织工作,在那里我们每周可以养活大约 700 个家庭。 司机们开始向东布鲁克林的家庭运送我们所谓的“爱心盒子”,其中包含农产品、个人防护装备和其他材料。 在鼎盛时期,我们在一个月内向 1,600 多个家庭送去了爱的盒子。
资金最终枯竭,我们意识到需要进一步组织。 一位朋友向我提出了一个系统概念,在该系统中,司机可以控制日程安排、行程和利润。
了解纽约市的行业规模很重要。 在大流行高峰期之前,仅靠拼车,纽约市每天就有近 80 万人次出行。 然后,如果你包括黄色出租车,你可以在这个国家最大的公共交通系统之上再增加 2 到 30 万辆。 每天都有数百万人穿梭于整个城市。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需要乘车的乘客和运送他们的司机之间的联系,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自己的应用程序。 最初,我们不知道如何获得启动该项目所需的资源和材料。
到 2021 年 3 月,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工作的不到十个人已经凑齐了一些钱,组织了 2700 多名司机。 我们还没有一个可以工作的应用程序。 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个承诺——我们通过 Zoom 开始了关于我们希望做什么的对话。 司机做出了回应。 我们能够利用它来产生动力,为我们赢得了大约 200,000 美元左右来获得一个非常基本的应用程序。 我们在五一劳动节推出,也被称为国际劳动节。
那个月晚些时候,我们在 纽约时报 以及其他一些左倾的网点。 我们利用这一点在发布后的一个半月内获得了超过 4 万次下载,然后开始了众筹活动,筹集了 140 万美元。 然后,我们获得了政府合同,并建立了现在按成员数量计算的全国最大的工人合作社。 截至 2022 年 2 月,我们现在的宇宙中只有不到六千名司机。
Source: jacobin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