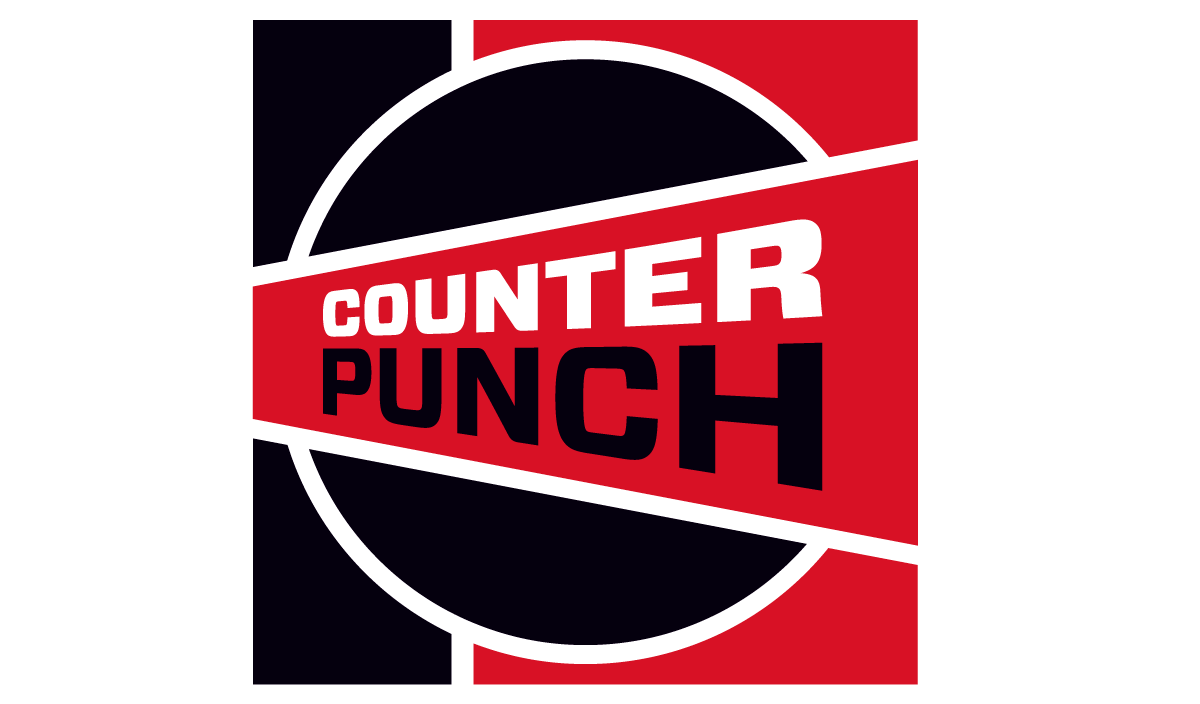
根据我对圣诞节的观察,圣诞节是普遍虚伪的大日子,人们声称彼此相爱。 富裕阶层宣传并假装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已经结束的时代已经到来。 而那些物质丰富的人突然变得精神起来,他们肚子饱了,吐出最好的救赎是灵魂的救赎。 对此我应该指出:反对独裁的激进分子为批评自己家里的兄弟情谊增添了一个理论上的理由。
我们在读恩格斯的著作 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 匆忙——就像我们所有的阅读一样。 他写道:“在家庭中,男人是资产阶级,女人代表无产阶级”。 因此,我们告诉自己,“个体家庭必须消失、被克服”,并带着这些态度继续前进。 我们对镇压时期的痛苦包括对同样受压迫的人——我们的亲戚——的愧疚。 如果上帝存在,那么我们当时的缺乏理解就应该得到原谅。 但我们也因为压抑家庭记忆的感受而遭受痛苦而受到惩罚。
因此,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在社会主义同志中寻求兄弟情谊。 在酒吧、海滩、会议和聚会上。 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找到了。 我在彼得·朗兹翻译的小说《永无止境的青春》中写道:
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好面对世界的邪恶。 我们互相谈论我们从未品尝过的美妙葡萄酒、芬芳的美酒、我们不会参加的盛大宴会。 我们要像野蛮人一样,用吊桥跨过护城河,猛攻资产阶级的城堡。 '布置桌面。 快点,在他们把我们扔到鳄鱼面前之前!” 我们不知道为获得感官的奢华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换句话说,我们要偏离良心的窄路多少。 我们还没有通过纯洁学徒期的第一个考验,尽管我们知道社会的顺从会奖励那些徘徊在魅力中的人。 但这并不等同于在考试或磨难之前放弃。 有一条像彗星尾巴一样炽热的发光线,将在1972年穿过那张桌子,并以光速行进到21日。英石 新千年之年。 我即将潜入那光的尘埃中。
扎卡雷利站起来,举起啤酒杯,仿佛里面装满了香槟,“我提议为我们的幸福干杯”。 我们本能地站起来,就像音乐会结束后公众跳起来一样。 为了我们的幸福! 为了更好的日子! 我们喊道。 我们周围桌子上的人都觉得我们很奇怪。 不过,这一次,语气里多了一丝同情。 就好像他们互相说:‘他们疯了,但那又怎样? 我们都很疯狂。 我们的玻璃杯叮当作响。 我们坐下来,互相微笑。 我们默默地互相交谈: 好吧,接下来怎么办? 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顺其自然。 然后我突然想到,要像我们感觉良好时总会出现的魔鬼一样说话:“我们真的有权利快乐吗?”
“马克思主义中没有任何东西会禁止幸福,”阿尔贝托说。
'我知道。 我问自己,当我们的一些同伴陷入困境时,我们是否有权利这样做。
'当然。 我们正在为斗争重振力量。”扎卡雷利回答道。
“但是当大多数人都处于如此糟糕的状态时,我们如何才能享受生活呢?”
“伙计,人们做爱,人们喝酒,人们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扎卡雷利说。
“同志,让我们跟随人民吧,”纳里尼亚说道,并对我眨了眨眼。
我站起来:“致人民!” 为人民干杯! 我们毫无悔意地共同接受享乐的权利。 我们感动地背诵卡斯特罗·阿尔维斯的诗句[1],“我的土地上金色和绿色的旗帜,巴西微风亲吻和摇曳”当我们结束时,我们互相拥抱。 我们四人围成一圈,旋转并跳到一首与 Wurlitzer 上播放的歌曲不同的歌曲“Alone Again”。
扎卡雷利在喧嚣中大声说道:“如果有一个世界桑巴、一个友谊桑巴、我的朋友们、一个新桑巴,那就太好了”。
过去是这样,但现在不再是这样了。 那些在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现在已经成熟了,不再轻率而肤浅地阅读《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 现在,他们在家里和其他地方拥抱他们所爱的人。 但我们仍然希望有一个充满真正兄弟情谊的新圣诞节。 这将会发生,或者应该发生,只有上帝知道什么时候。
笔记。
[1] 安东尼奥·弗雷德里科·德·卡斯特罗·阿尔维斯(Antonio Frederico de Castro Alves,1847-1871 年)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效仿济慈或巴西同胞音乐家/作曲家诺埃尔·罗莎(Noel Rosa,1910-1937 年),在巴西的社会文化和艺术领域闪耀着光芒。 20多岁时死于肺结核。 卡斯特罗·阿尔维斯出生于巴伊亚,14 岁开始在累西腓学习。曼努埃尔·班达拉 (Manuel Bandeira) 称他为“一个真正崇高的孩子,如今他的作品的社会意图重新焕发了他的荣耀。”
Source: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23/12/25/for-a-new-christm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