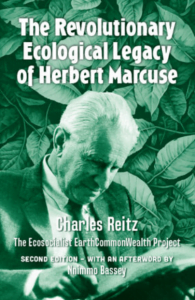8 月 29 日,拜登政府宣布了 10 种药物清单,医疗保险将根据去年《通货膨胀减少法案》授予的新权力首次对其价格进行谈判。 据政府称,仅 2022 年,服用这 10 种药物的 Medicare 参保人就总共支付了 34 亿美元的自付费用,而 Medicare 的费用总计为 500 亿美元。
新价格将于 2024 年 9 月公布,但要到 2026 年才会生效。拜登在声明中宣称,“我们将继续对抗大型制药公司,我们不会退缩。” 新的言论与奥巴马政府对制药行业更加宽容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由于担心该行业强大的游说影响力,政府标志性的医疗改革——《平价医疗法案》使强大的制药行业毫发无伤。 不出所料,药品成本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已成为医疗保健成本中增长最快的组成部分。
毫不奇怪,大型制药公司正在对抗拜登政府的努力,发起诉讼以阻止新规则的实施。 与此同时,作家们在 经济学家 同样不足为奇的是,他们在大型制药公司需要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 尽管承认美国人确实在毒品上花费过多,但《报纸》还是抱怨新的“严厉”规则“已经从一个极端转向了另一个极端”。
究竟是什么如此极端? 这 经济学家 认为,由于拒绝谈判的处罚是征收高达产品销售额 95% 的消费税,因此 Medicare 官员与其说是在谈判价格,不如说是通过命令制定价格。 此外,如此严格的价格控制最终将损害我们所有人,因为支付高价购买受专利保护的药物是我们资助制药创新的方式。 由于开发新药风险大、成本高,制药公司只有在承诺获得巨额利润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做。 如果没有这些巨额支出,该行业就缺乏进行研发 (R&D) 并将新疗法推向市场的动力。 至少理论上是这样。
他们是对的吗?
让我们暂时承认一个相当夸张的说法,即谈判规则实际上等同于政府价格管制。 大型制药公司真的是下金蛋的鹅吗?价格管制会杀死它吗? 争论的核心是,通过故意多付药品费用,我们正在为创新提供资金。 如果这是真的,我们预计大型制药公司将积极将其留存利润再投资于研发支出。
去年,按收入计算,美国三大上市制药公司辉瑞、强生和默克的研发支出总计达 396 亿美元。 不可否认,这是很多钱。 但通过谈判仅十种药物就能节省的费用还不到医疗保险的费用——节省下来的费用可以简单地交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以直接资助研发。 此外,这些公司通过股息和股票回购向华尔街输送了几乎同样多的资金,达到 357 亿美元。 他们还找到了 401 亿美元(仅现金)用于收购其他现有的制药公司。 这还不包括用于说服医生和患者购买其产品的臃肿营销预算。 如果这些公司的账簿有任何迹象的话,那就是在新药研发上投入资金并不是大型制药公司的首要任务。
事实是,最大的制药公司根本不是真正的药物开发公司:它们是拥有专利组合的营销、游说和诉讼公司。 虽然大型制药公司拥有大量处方药现有专利组合,但创新管道 新的 药品实际上与大型制药公司关系不大。 事实上,公共资源——尤其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取得科学突破的基础研究。 然后小型精品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利用公开产生的知识进行最后阶段的研究,例如进行临床试验,将药物推向市场。 小公司在新药供应中所占份额巨大,而且仍在增长。 现在,三分之二的新药来自这些小公司,而二十年前只有三分之一。 开发新药的并不是辉瑞公司的研究实验室。
事实上,通常只有当一种经过验证的药物已经存在时,大型制药公司才会介入。 这些公司凭借销售受专利保护的现有药物而获得的雄厚财力,购买了那些已开发出经过验证的获胜者的公司及其专利权。 换句话说,大型制药公司并不预先投资开发新药;而是进行投资。 它在最后介入,帮助精品公司的早期投机投资者套现。 作为 金融时报 最近表示,“大型制药企业别无选择,只能进行并购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因为他们必须填补药物管道中的创新空白。”
一旦收购了创新者,大型制药公司真正的竞争优势就会发挥作用:营销、政府关系和诉讼。 毕竟,正是大型制药公司可怕的游说力量使奥巴马医改远离了该行业的利润。 在诉讼方面,大型制药公司利用法院采取“拖延付费”等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即公司起诉仿制药制造商侵犯专利权,然后向他们支付费用,以使药物在市场上停留更长时间。最终解决。 大型制药公司还擅长以其他方式博弈专利和其他监管排他性——通过诸如常青老药(例如,将药物从胶囊改为片剂)和不加区别地申请专利等手段,后者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行走以最大化专利保护的期限。
至此,我们可以勾画出鲁布·戈德堡机器的轮廓,通过该机器,支付过高的药品费用有望带来医疗创新。 我们故意向大型制药公司多付了专利保护药物的费用。 虽然这些垄断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华尔街,但其中一些却流向了大型制药公司收购规模较小的创新制药公司——华尔街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当然会在这一收购过程中分一杯羹。 最后,该论点认为,小型创新者正是依靠这种收购的期望来激励自己进行困难且昂贵的临床试验。 因此,如果医疗保险挤压大型制药公司的利润,所有创新的动力都将丧失。
现在,开发新药确实充满风险且成本高昂。 它确实需要某种公共补贴,美国在供应方(NIH 研究)和需求方(专利保护、医疗保险不协商的所有价格)都提供这种补贴。 如果我们不通过支付过高的药品费用来补贴制药公司,我们就必须以其他方式为创新提供资金。
是否有其他融资创新模式? 经济学家迪恩·贝克(Dean Baker)早就指出了一个明显的替代方案:我们可以直接自己支付从基础研究到商业化的研发费用,而不是我们现在拥有的鲁布·戈德堡垄断机器。 正如贝克指出的那样,制药公司是 NIH 药物研究公共资助的最大支持者,他们非常依赖并重视这些研究。 但他们也坚持将临床试验阶段私有化——似乎认为那些同样出色的 NIH 研究人员在那时突然变成了无能的黑客。
此外,即使我们相信私营部门在创新方面更有效,但为药品支付过高的费用远不是利用私营部门谋求公共利益的最明显方式。 政府可以不采用专利垄断和医疗保险补贴,而是简单地与大型制药公司目前目标收购的小公司签订合同,并省去中间商——付钱给他们开发药物。 军工联合体通过类似的采购流程开发毁灭性创新的能力几乎没有受到阻碍; 为什么救生创新会有所不同?
最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推动药物开发的市场激励措施可能对医疗保健行业弊大于利,因为市场价格大大低估了社会福利。 例如,目前制药公司的动机是开发治疗慢性疾病的药物,甚至是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等相对不严重的疾病,而不是治疗危及生命的疾病,毕竟这些疾病只需要治愈一次。 在最近严重的埃博拉疫情期间,公众的注意力短暂地集中在制药业未能开发出有效的疫苗或治疗方法上。 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痛斥制药业,指责该行业的营利性质导致其未能投资于危及生命的疾病的治疗。 “研发激励几乎不存在,”她说。 “以利润为导向的行业不会为无法支付的市场投资产品。”
目前,我们通过向大型垄断企业投入巨额资金来支付医学创新,然后希望有足够的资金流向实际进行创新的生物技术研究人员,以激励持续的研发。 如果我们从头开始设计一个创新的生态系统,我们就不太可能创建这样的生态系统。 事实上,当我们需要快速疫苗来对抗 COVID-19 疫情时,我们使用了一种基于直接融资的完全不同的模式。 我们有鲁布·戈德堡垄断机器的可行替代品。 有鉴于此,拜登政府新规定的一大风险在于,这些规定的生效时间太长,或者力度不够。
当前的体系显然对于发挥大型制药公司的力量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体系:利用现有专利组合中的垄断租金,公司可以继续购买将提供下一代垄断租金的专利。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该系统实际上是资助救生药物创新的最佳方式。
Source: jacobi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