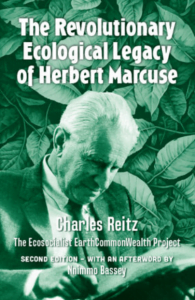图片由戈登·考伊拍摄。
“那时候我就知道说唱永远不会消亡”
-KRS-One – 离开这里1993“所有的诗歌都向往嘻哈歌词的状态”
-格雷格·泰特 – 复活与光2004
聚集在你选择的屏幕的苍白电火周围,我会告诉你最后诞生的鲜活文化的故事。
它是由珍贵的碎片和幸存的残余物、垃圾、痛苦和忽视,以及在痛苦的旅程中得到精心照料的传统珠宝组成的。 在暴行和绝望的滋养下,在混凝土和铁丝网的滋养下,它的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穿过中间的通道、种植园、世界大战和臭气熏天的小巷。
那颗种子恰好在世界末日到来时到达。 它生长在南布朗克斯的水泥土壤中,那里连武装执法者都不愿踏足。 婴儿的死亡率比这片土地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暴力流氓团伙统治着街区,公寓大火熊熊燃烧,瓦砾吞没了街道。
然而那里的人们又唱又跳。 他们开玩笑、调侃、浪漫。 为租赁派对录制的唱片。 有酒、大麻、海洛因、电视和迷幻药。 和平先知的鬼话在项目走廊里回响。 午夜掠夺者在火车车厢和灰色墙壁上绘制了精美的壁画。 唱片骑师在公园里为人群大肆宣传。 孩子们在纸板上旋转。 这些人是被遗忘的人、被压迫的人、被忽视的人、绝望的人。 但他们还活着。 他们竭尽全力,茁壮成长。 他们在废墟中创造了文化。
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有一个名叫克莱夫的年轻人。 他的家人来自杜布和恐惧之岛。 当他跨越了从童年到成年的看不见的边界时,他长大了,直到他比周围的其他年轻人更大、更高。 由于他们的人性因压迫而变得不经意的残酷,他们因他的不同而蔑视他。 正是他们给他起了赫拉克勒斯的绰号。
但他比尼奥早了一步。 他对这个绰号进行了改造,变得家喻户晓,然后举世闻名。 大家都知道,Kool Herc 在他的两个转盘上只播放了唱片中最好的部分。 Herc 演奏了 休息时间。
第一次失败是在他妹妹的筹款聚会上,现在故事的讲述者称之为整个文化的生日。 8月11日th1973年,在南布朗克斯塞奇威克大道1520号,嘻哈文化诞生。
***
最好的故事即使不关心事实,也会讲述真相。 为一种文化庆祝生日对于原声摘要来说是很整洁的,但这一切都取决于你对文化的定义。 毕竟,自从有人和墙壁存在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墙上画画。 自从詹姆斯·布朗翻转麦克风支架,自从罗伯特·约翰逊站在十字路口,自从奴隶船起航,自从骚乱者在西非的风景中漫步,自从第一个故事围绕着火被讲述以来,说唱就一直在进行。
至于舞蹈和节奏? 他们是永恒的。
***
我几乎是嘻哈音乐从纽约民间文化向全国流行文化转变的同时代人——第一个说唱大热门, 说唱歌手的喜悦 由 Sugarhill Gang 创作,于 1979 年出版; 我出生于 1980 年。整个 80 年代,我听到隐秘种族主义者告诉我说唱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时尚。 上世纪 90 年代,我看到一些知名政客在电视上大肆宣扬这种凶残的丛林音乐的罪恶。
早在 E-40 和 Too Short 成为湾区大使之前,我就开始关注他们了。 我记得当 2pac 还是一名巡演人员时,当 Notorious BIG 成为第一个真正吸引我耳朵的纽约说唱歌手时——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都在二十多岁时被谋杀。
***
85 年或 86 年左右的某个时候,我的父母突然转向有线电视,这对我来说意味着 MTV。 我忍受了好几个小时繁琐的广告和令人忘记的视频,热切地等待着神圣的时刻,最后,Run DMC 和 Aerosmith 将到达电视祭坛并宣讲他们的布道。 走这边, 黑人说唱歌手和白人摇滚歌手一开始是竞争对手,然后打破了他们之间的隔阂,在音乐会上合作。
对于一个居住在郊区的混血孩子来说,一次很少和超过三四个黑人在一起,这就像看着我身份冲突双方之间的墙倒塌一样。 早在我知道摇滚乐是黑人音乐之前,早在我的耳朵解码查克·贝里吉他即兴演奏的 DNA 之前。
这堵墙被白人摇滚乐手和黑人说唱歌手的联盟象征性地摧毁了……那堵墙是由资本主义建造的。
***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不会唱歌或演奏任何乐器,但我可以记住并吐出那些随着节拍跳舞的韵律。 我被迷住了,着迷了; 我曾是 在下面 拼写。 它从来没有坏过。
生来就是血友病患者,我太害怕了,不敢尝试霹雳舞,尽管我渴望那种优雅、力量和杂技技巧。 我太害怕法律而不敢涂鸦。 如果有人把我放在一副 Technic 1200 面前,让我擦擦唱片,我肯定会这么做,但在我有机会尝试之前,我就已经三十多岁了。 到 2018 年,我已经熟练到毁掉了我的 Bobbie Gentry 的主打歌 想要 LP,为我专辑中的一首歌做搓盘 墙上的蜘蛛。 这是完全值得的。
***
由于我是独生子,没有真正的社区可言,所以在我的童年里,嘻哈是一种独奏的乐趣。 我错过了很多里程碑——Rakim 改变游戏规则的音乐流、NWA 的帮派吹牛、听到完整的突破性早期专辑而不仅仅是孤立的广播单曲时的兴奋。 作为湾区的孩子,我用自己的钱买的第一张专辑当然是湾区乐队:Digital Underground 的 性爱包……现在我想起来,这对我成年后的浪漫生活的影响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大。
直到高中,我才开始与朋友们交易说唱专辑,他们都是白人男孩,后来我发现他们一直是音乐产业的目标市场。 我不会在意; 如果那个爱尔兰姓氏的孩子有新的 Bone Thugs & Harmony CD,那么该死的我会和他联系以获得盒式配音。
***
几年前,我和一位二十多岁的朋友在一场愚蠢的辩论中,他在谈论 LL Cool J。听着,我知道你在那个戴着 Kangol 帽子的黄色 MC 变成了一个老套的警察之后很久就已经成年了。表演演员,但请年轻人不要当面; 这是 你的 不幸的是,你永远不会知道第一次听到那些在电波中传出的歌词有多么强大——没有说唱歌手能像我一样说唱/我会带一个肌肉发达的男人把他的脸埋在沙子里! 在千禧一代和变焦族的可悲的控制论反乌托邦中,没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了,而且永远不会。 那个时间已经结束了。 抱歉你错过了。
***
当世贸中心消失在有毒尘埃中时,嘻哈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超级商品。 1996 年的《电信法案》放松了对广播的管制,直接导致所有大型媒体卡特尔收购和/或粉碎无数蓬勃发展的独立唱片公司,然后将说唱同质化为 Gangsta Shit™。 这种子流派一直对说唱最大的购买群体——16 至 24 岁的郊区白人孩子——最具吸引力。
我会让读者思考为什么这些人群会被由此产生的暴力、厌恶女性、趾高气扬的桑博漫画所吸引。
***
每当我看到有人将埃米纳姆列入史上最伟大说唱歌手名单时,我都会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冲动,想要点燃一些东西。 甚至不要跟我谈论 8英里。
***
我的政治和哲学倾向深受德里克·詹森(Derrick Jensen)和哈基姆·贝(Hakim Bey)作品的影响,但我在巴比伦永远举起的无政府主义中指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被黑豹之子图帕克·沙库尔(Tupac Shakur)激活的。
***
2003 年,我偶然发现了洛杉矶历史上最热闹的嘻哈舞会场景。 我即将大学毕业,却不知道如何谋生,所以我参加了调酒课程。 我向我的一个功夫兄弟提到了这一点,他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前海军陆战队员和建筑工人,兼职在洛杉矶唐人街的大星爵士俱乐部当保镖。 他告诉我他们正在寻找一位新的调酒师,然后递给我古老的老板弗兰克(RIP)的电话号码,他在第二次响铃时接听了我的电话,并给了我一生中最简短的采访: 周六晚上 9:30 你能来吗? 是的。 回头见。 *点击*
我在巨星工作的六年永远改变了我的生活。 就在那里,在舞会上 鞭炮,在那里我听到了当地音乐的守护神 J Dilla 的音乐。 这远早于 YouTube 或流媒体广播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对你进行教育。 我开始收集黑胶唱片和自行出版的杂志。 我和各个种族的漂亮女人都发生过关系。 我用笔记本写歌词,把混音带放在一堆里,然后在当地的演出中表演。 我成为了一名忍者超级英雄。
即使在好莱坞迫在眉睫的阴影和随之而来的废话中,嘻哈作为当地民间文化的遗产仍然在大星酒店继续存在。 我是一个独特而神奇的、一个真正的社区的一部分——最好的事情是, 我 知道。
***
节奏与韵律的舞蹈是一口永不枯竭的井。 当歌词落下并包裹在鼓和旋律中的那一刻,没有什么感觉如此宏伟,没有什么匆忙如此令人满意。 它把我从绝望中拯救出来,把我从自杀中拯救出来。 我的一生都归功于嘻哈音乐。
***
嘻哈作为一种活生生的民间文化现在已经基本灭绝,被企业掠夺和网络技术所扼杀。 当用手机录制节目的人数多于在空中挥手的人数时,聚会就正式结束了。 文化已成为数字拟像。
如今,人们与机器联系而不是建立关系,言语在电子白噪音的深渊中失去了所有意义,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选择,而(反)社交媒体已将每个人变成了自己的品牌™。 对于文化和社区等古色古香的遗迹来说,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
看看“太晚的资本主义”的结局吧——一个充满了零维僵尸的网络世界,他们迷失在孤独中,被屏幕吞噬一切的眼睛所吞噬,忽视或因全球变暖的恐惧而畏缩。 瓦克斯比比皆是。
***
十多年来,我尽最大努力挑战这种机械性的弊病,通过消除技术中介的经验来保持当地嘻哈民间文化的活力。 它过去挺美。
然后瘟疫来了。
***
然而我还是站了起来。 最近,我在嘻哈之旅中实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经过这么多年的歌词创作,我终于开始制作自己的节拍,今年夏天我在我完全自己制作的第一个节拍上录制了一首歌。 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险恶时代来说,这是对我最喜欢的反乌托邦科幻小说《疯狂的麦克斯》系列的改编。 你可以在这里听它。
***
多年来平均下来,我几乎没有从我所有(许多)说唱专辑的总销量中赚到零花钱……但嘻哈音乐 文化 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支付我的账单。 首先是 Grand Star,后来我花了六年时间在公立学校教授嘻哈讲习班。 新冠疫情扼杀了这一点,自 2020 年以来,我一直担任保安; 我通过一位朋友得到了这份工作,我是通过我的兄弟 Q-Digs 认识的,我第一次见到 Q 是在旧金山的一个嘻哈舞会上,当时我把我的一张专辑递给了他。
***
停不下来。 不会停止。
Source: https://www.counterpunch.org/2023/09/01/folk-culture-of-the-end-times-reflections-on-hip-hops-50th-anniversary/